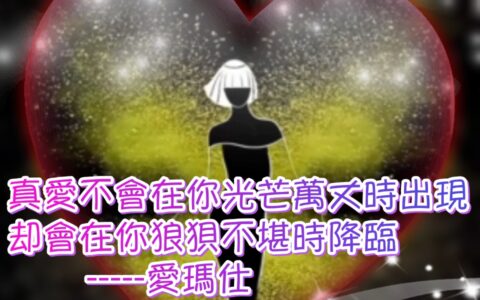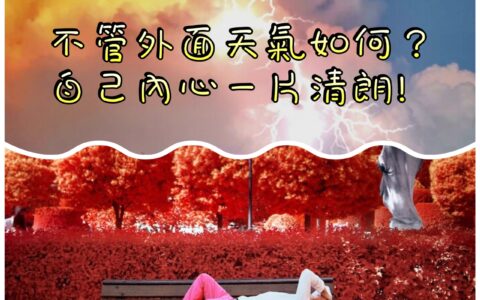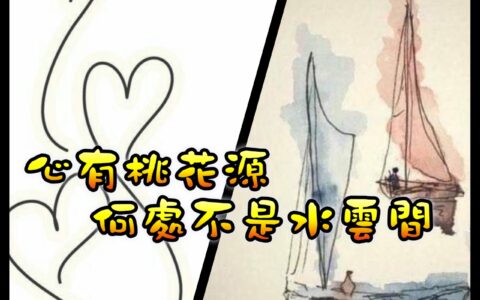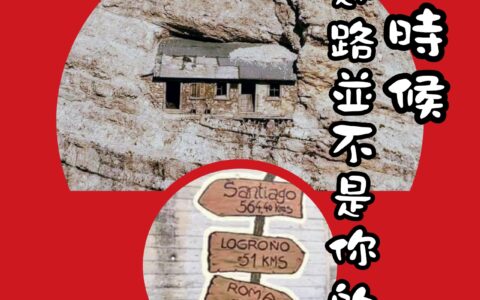以「破壞式創新」理念,走向藍海市場
2home.co 楊惟婷
美國獨霸全球,是不容許任何國家、企業挑戰美企龍頭地位。
若有任何國家、企業敢捋美國虎鬚,雖遠必誅。
「威盛」也好,「宏達電」也好,「華為」也好,「寧德時代」也好,「比亞迪」也好,若對「美國第一」有所威脅,雖遠必誅。
一、「英特爾」如何絞殺「威盛」?
談起威盛電子(下稱威盛),想必大部分的人都不陌生。
威盛電子是無晶圓、低功耗X86處理器平台先驅,目前市占全球排第三,也是個人電腦、終端機、超行動裝置與嵌入式系統市場的領導廠商。
但在2000年,威盛的南北橋晶片組(電腦CPU、中央處理器),一度挑戰英特爾龍頭地位,並成功拿下全球市佔率一半,也在台灣股市創下629元的天價,榮登台股股王,市值高達1兆8千多億,有「台灣英特爾」之稱,美國當然雖遠必誅。
2001年,當時英特爾(Intel)發動訴訟戰,雙方纏鬥近三年之後,在形勢比人強之下,威盛被迫簽訂10年技術授權合約,導致威盛的晶片組技術不再是獨家生意,這讓威盛頓失市場優勢。
在美方的逼迫下,威盛只好開始思考轉型的路徑。
由於英特爾封殺威盛的生路,讓威盛只好轉戰「嵌入式」平台市場。
威盛認為:「未來的資訊應用,將從運算導向轉入連結導向,重視的是寬頻的有線連結以及區域的無線網路,而這些應用將帶動嵌入式系統的需求。」
2012年,威盛又決心切入需求日漸攀升的AI領域。
檢視威盛的成績,截至2023年7月為止,累計合併營收達50.82億元,創下14年以來同期新高,年增率為32.6%。
■威盛開啟轉型二部曲
從跌倒、爬起、再轉身,一路的過程當然不簡單。
第一步:切入嵌入式平台市場
嵌入式電腦應用於控制、監視或輔助設備、機器或甚至工廠運作的裝置,這些場景在運算設計上也有別於一般電腦,需要能符合各種商用的需求,軟體還要能調整,威盛表示:「嵌入式和PC最大的不同,就是軟體比硬體還重要。」威盛也因此招募了許多軟體工程師。
嵌入式平台的發展,替威盛累積了一定的運算基礎和軟體人才。
然而,該如何運用這股力量,卻一直沒有解答。
即使,公司內部都知道要朝AI轉型,只是怎麼轉、要往哪裡轉,卻一直都是難以回答的問題。
第二步:人才、技術到位,強攻車載應用
幸運的是,威盛在2015年迎來了轉機。當時日本最大的計程車隊Japan Taxi看準威盛軟硬整合的能力,找上威盛發展智慧物聯網計程車系統,整合包含電源管理、導航優化和搜集車隊數據等項目。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,威盛開始認定,「車載應用」會是未來的重要應用。
綜觀來看,從CPU起家的威盛,本身就擁有IC設計能力,加上長年在嵌入式系統軟體技術的耕耘,包含影像及人臉辨識,能夠整合軟、硬體。而這樣的優勢,是威盛在轉型路上相當重要的武器。
■威盛切入「車載應用」兩大優勢
在確認即將發展「智能產品」後,威盛也在2022年將嵌入式事業部改名為「智能產品事業部」,由吳億盼持續領軍。目前旗下主要產品包含智能車載、智慧工業、智能建築以及智能邊緣(AI邊緣裝置發展工具)
有了物流車隊的基礎,威盛也持續探索更廣闊的市場。
以堆高機為例,威盛近年在中國擁有不少訂單,包含長城汽車、雙葉汽車零件等都是客戶。在威盛的智能產品中, Mobile360系列中的AI雙向行車紀錄器,除能記錄堆高機前方的影像外,也可對內透過AI偵測駕駛是否有打哈欠、不專心等情形,還會發出警示音以提高駕駛警覺 。
堆高機雖然相較一般轎車規模較小,但仍具一定規模, 中、美現在都各有百萬台的堆高機,是一種百萬級的應用。 吳億盼也總結出兩項威盛能夠站穩市場的重點:售後服務和精準AI模型建造。
優勢1:AI模型、軟體持續更新,讓安全性維持同一水準
首先,既然轉型,商業模式自然也會跟著改變。在此,售後服務指的是安全性是否能持續維持在同一水準,包含讓客戶了解如何更新軟體、AI模型是否能與時俱進等等。
其中重要性在於,隨著ESG(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、社會責任Social、公司治理governance)重要性提升,工廠內部的員工安全,也被納入治理(governance)評估的一環,而威盛的系統能提升安全性,幫助客戶達到ESG中『治理』這塊的需求。
優勢2:建立精準判定的AI模型,減少客戶使用麻煩
威盛從找出自身在運算設計的優勢,到瞄準物聯網的戰略轉向。其中,精準的模型建立,尤其一定要讓判定很精準就是成敗關鍵。
那麼,威盛的AI模型是怎麼建立的呢?
例如,威盛的技術能透過少量的樣本,做出大量的情境模擬,再透過這些情境來生成AI模型,這即是威盛的核心技術之一,所以即使別人做得出類似的競品,只要他的AI沒有威盛的精準,威盛就有護城河在。
不過,由於工程車輛的形狀都不同,要達到精準其實不容易,例如日本的堆高機,操作人員都是站著,跟美國坐式不同,所以威盛的錄影角度就必須要能調到符合才行。亦即,必須從實際的應用現場察看狀況,以瞭解客戶真正的痛點在哪,才能回頭來優化產品。
從物流、堆高機站穩腳步後,威盛又進一步進軍「重型設備」市場,希望一網打盡所有商用車量,例如工程車的應用場景。
其中,礦場的採礦車一台近乎10公尺,相當於三層樓高,有好多的死角都是難以想像的。人一站上採礦車,根本看不見方圓幾公尺內的物品,加上採礦場通常都是漫天飛沙,能見度低,倘若移動中的機台旁邊站著其他工人,稍未注意後果將會不堪設想。這也是為什麼,精準的AI辨識在礦場這樣險惡的環境中,更為重要。
那麼,商用車市場的規模究竟多大呢?吳億盼分享,汽車後裝市場約有10億台,威盛則瞄準其中約3億台以上的商用車商機。
例如像開拓重工(Caterpillar)的重型工業設備,就會使用到威盛的產品。
另外,威盛的車載視訊系統已切入日系車廠供應鏈,並已開始與AWS(亞馬遜網路服務)聯手合作,建置雲端平台。
■威盛「處理器技術」助攻,「兆芯」推出KX-7000系列處理器驚艷外媒
美國2022年10月開始對大陸祭出晶片出口禁令,迫使大陸朝「晶片自主化」目標邁進,威盛電子與上海市政府共同成立「兆芯」,2023年12月底推出KX-7000系列處理器。此大陸史上最強自主研發中央處理器(CPU)「KX-7000系列」引發關注,因該款新晶片運算效能是上一代KX-6000的兩倍速,是大陸目前運算最快的CPU,可望成為擺脫對西方技術依賴的關鍵。
雖然威盛受「英特爾」絞殺下,多年來在CPU領域影響力不大,但其仍是全球3家擁有x86架構許可的公司之一,另外兩家為英特爾與超微。而KX-7000目前是大陸「晶片自主化」後製造的最快速CPU。
雖然KX-7000與其x86競爭對手相比並不特別出色,包括超微中階CPU Ryzen 7 7700X與Core i5-13600K的時脈速度,都比最高階的KX-7000快許多。但對大陸來說,KX-7000能否擊敗對手不是重點,終極目標是擺脫對西方技術的依賴,以達成科技自主。
兆芯透露,KX-7000已獲得大陸主流整機廠商聯想開天、同方、紫光、升騰、聯和東海等採用導入新品,大舉搶攻大陸內需市場。
二、「Apple」如何絞殺「HTC」?
一支智慧型手機裡面,究竟有多少專利?例如,Google在跨入手機市場前做了調查,一隻手機大約有25萬個專利權利項,所以在科技產業的爭霸戰中,專利戰成為有效克敵制勝法寶,尤其在美國老大撐腰下,Apple對手常會遇上「禁售令」,只能將市場拱手讓人。
在蘋果電腦(Apple Inc)於2010年3 /2日控告宏達電(HTC)侵犯其 20項專利後,宏達電也反擊了,在美國時間 2010年 5 /12日宏達電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(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;簡稱『ITC』)提出對蘋果的專利侵權訴訟制裁,訴訟內容主張蘋果電腦產品侵害宏達電五項專利,請求 ITC禁止美商蘋果電腦進口及於美國販售 iPhone、iPad 及 iPod產品。
2012年11/11日宏達電(HTC)與Apple發布聯合聲明,解除長達32個月專利訴訟戰,HTC與Apple雙方達成和解,將撤銷全球所有專利訴訟糾紛,並簽署為期十年之專利授權契約,範圍涵蓋雙方現有與未來所持有的專利。
如同威盛電子所遭遇的命運,「宏達電」一旦成為「Apple」的威脅,「宏達電」的悲慘命運,就已註定。
■Apple vs. HTC訴訟戰背景
HTC的「蝴蝶機」一度風靡全球,挑戰Apple龍頭地位。
Apple自2010年3/2日在美國啟動「專利戰」以來,APPLE與HTC之間長達32個月訴訟纏戰,從美國打到英國及德國,從智慧型手機打到平板機,Apple從專利侵權到「禁售令」攻擊,萬箭齊發,絕不手軟。
2011年正當宏達電與蘋果的「專利戰」正打得火熱之際,威盛也加入戰局控告蘋果,隨著2012年11/11日HTC與Apple率先達成全球訴訟和解之下,四天後11/15日威盛及S3G也與Apple達成和解,解除訴訟糾紛。
這場看似一場「不對稱」之戰爭,HTC vs. Apple小蝦米力抗大鯨魚的劇碼,從雙方在美國ITC及聯邦法院共發起12件訴訟案,其中還包括一項是HTC被Apple指控違反Anti-trust案。雖然,Apple共拿出34項專利打擊HTC,而HTC僅被判有一項專利 (US5,946,647,data tapping功能)侵犯Apple,但也被美國ITC發出「禁售令」,造成宏達電推出新機種受影響,從此一蹶不振。
最後,Apple考慮Android作業系統市佔率已高達75%,已成為手持裝置廠商及消費者的選項之一,是無法抵擋的事實,因此APPLE願意與HTC達成全球大和解。其中盤算:
1、Apple企圖扭轉與Android陣營對立的形象
Apple先後與IBM、Microsoft、Nokia達成專利交互授權,避免市場壟斷的指控,但是,就是尚未與Android陣營的廠商達成交互授權,而HTC是Android陣營中最佳選擇。
2、Apple企圖擋住Android其他大廠的壯大
對Apple而言,三星已養虎為患,中國後起之秀中興及華為是隱憂,Android陣營須要技術能量不差的HTC來擋住後進入者。
3、Apple想專心集中火力對付Samsung
Apple vs. Samsung專利大戰仍在進行,Samsung才是Apple的頭號敵人。全球智慧型手機市佔率,Samsung已高達31.3%,Apple還停留在15%。
4、HTC藉外籍兵團搬救兵爭取籌碼,換得與Apple交互授權的機會
HTC向第三方大量購買具攻擊性的專利武器充實彈藥庫,包括從S3 Graphics、HP、ADC及Nokia等,外購不少所謂的通訊標準必要專利(SEP),這些SEP專利也是Apple有興趣想交互授權的部分。
5、Apple謀求日後向Android陣營收取專利授權金,爭取最佳價值標準
在8月24日Apple vs. Samsung 世紀大審判出爐不久,已傳出Google與Apple的CEO透過電話進行專利交互授權溝通的消息。Apple藉由先與”相對小咖”HTC談妥授權金和解,將來可藉此向”大咖”Samsung收取較高授權金,當然這也包括其他Android手機廠。
■HTC戰後餘生
在長達三年的「專利戰」後,HTC錯失成長良機,在智慧型手機的毛利已大不如前,加上Samsung已遙遙領先Android陣營群雄,中國的華為及中興已追趕上,HTC市佔率也只剩4%左右。
而華為及中興走中階低價策略又有中國市場支撐,HTC想回到2008年20%毛利似乎已經是「回不去了」。和解後,HTC授權金已墊高了成本,從此一蹶不振。
原本,宏達電是美國智能型手機市場中Android的王者,但在蘋果的專利戰強攻下,宏達電的確遭受到了壓制,蘋果表面上看起來得到勝利,但實際上,並未從這場專利大戰中獲益。
值得一提的是,Apple對HTC啟動專利戰爭後,Apple市占率並沒有因為訴訟增加,反而讓三星變成最大受益者,使三星的北美市占率從8%提升到31.3%,這也使得智慧型手機爭霸的局勢,更複雜地分化下去。
雖然Apple在2012年接著對三星啓動專利戰爭,也打了一場獲賠逾10億美元的大勝仗,但對不缺現金的蘋果來說,這只是贏了面子,三星的市佔率並未因此而下降。此外,在Apple、三星兩強對決時,蘋果無法佔上風的原因,乃Apple與三星分屬兩個不同的操作系統,消費者若不買蘋果操作系統,Android就是唯一的選擇,這也是三星倖存、壯大的原因。
三、「聯發科」從山寨走向世界的大志
或許「威盛」、「宏達電」小蝦米力抗大鯨魚的悲慘際遇,給了「聯發科」警惕,因此,「聯發科」選擇了「快老二」戰略,默默地由山寨走向世界的舞台。
手機晶片企業「聯發科」在2020年營收創新高、成為全球第三大IC設計公司,其淨利逾400億元,更較2019年大幅成長8成。並傳出打入蘋果供應鏈,為旗下品牌耳機供應晶片。
最讓外界瞠目的是,2019年第三季,聯發科成立23年以來,第一次攻占全球手機晶片市占率第一,超越穩居此王位多年的巨人高通(Qualcomm)。曾經「山寨」起家的聯發科,正在逆襲超越「高通」,試圖稱霸全球手機晶片市場?
相較於3G時代,「聯發科」技術落後高通至少5年、4G時代落後至少2年;在5G時代「聯發科」已經躋身技術領先梯隊,甚至於2019年底搶先高通一週,發表5G手機晶片!
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跟執行長蔡力行做了什麼,能讓這家過去被外界貼上「山寨」標籤、「低價」導向的公司,開始能主張「價值」,取得高毛利?
■「聯發科」擅長「快老二」策略
以往,「聯發科」擅長「快老二」策略,意指公司不一定是首先推出該類型產品者,但在產品逐漸成熟後,它透過快速模仿領先者,用更短開發時間、更大量產規模或技術與服務創新,推出「更高性價比」的產品,晉升「市場第二名」。
「聯發科」從創業初期的「光碟機」到中國的「白牌手機」之戰,它都靠此「快老二」方程式致勝。但它在4G時代卻挫折連連,原因無它,「快老二」拚的是時間,但手機這領域,規格更迭太快了!
更挑戰的是,它的客戶群如小米、Oppo、Vivo也都開始想升級,不甘於只標榜性價比,這逼得聯發科也必須從打「價格戰」,認真往「價值戰」升級邁進。
以上種種負面因素,讓聯發科在2016、17年陷入低谷。那2年,該公司毛利率僅35.6%,是創業以來最低,營業利益率最低更僅剩4.1%。當時市場一片看空「聯發科」,其股價甚至跌破200元,創金融海嘯以後新低。
但在2016年股東會,蔡明介在公司最黑暗的時刻,喊出未來5年要投資2000億元在5G跟AI等技術上。這數字,是它當年稅後淨利逾8倍。
當時5G有兩種規格:一個是較低階,但較容易從4G轉換、市場將率先導入的「Sub-6」;另一個則是能真正實踐5G車聯網、工業物聯網等高階應用,但難度較高、市場導入時程較晚的「毫米波(mmWave)」。
「聯發科」選擇優先發展『Sub-6』的策略,也就是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,專注於優先發展一種規格,這樣跟高通的距離就拉近了。
2017年,蔡明介邀請素以執行力著稱的蔡力行出任共同執行長。熟稔晶圓代工產業的蔡力行,能讓聯發科在研發路徑上更精準,因蔡力行很懂台積電每個製程節點是在幹什麼,這肯定幫聯發科加分。
2019年5月中美貿易戰爆發,美國正式將「華為」與70家關係企業列入「實體清單」,迫使華為及旗下IC設計公司「海思」退出手機晶片舞台,並限制高通、英特爾等企業與他們來往。這讓眾多中國手機品牌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被制裁目標,提前分散晶片供應來源,從高通轉單聯發科。
「海思」被迫退出手機晶片舞台後,目前5G手機戰場上僅剩高通和聯發科兩大玩家,未來較高規格的毫米波,聯發科也已經布局,且5G以外的物聯網實力也齊備了。因此,聯發科因禍得福。
■聯發科走向「平價奢華」的「破壞式創新」策略
聯發科從「快老二」策略,也不斷調整自己的營運策略;如今,聯發科走向「平價奢華」的「破壞式創新」策略。
「今日山寨,明日主流。」是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的名言,至今仍紅遍中國3C市場。事實上,「聯發科」手機晶片組和整體解決方案的進化,正是手機生態系統的發展史。
跟國際品牌手機相比,山寨機的生產流程更精實敏捷,當山寨機廠商有新產品的構想時,可採用聯發科的整體解決方案包括仿真器和模擬器等設計工具,以其公版設計為基礎再進一步修改客製化,選定所需的聯發科晶片組並採購其他零組件,再進行開模、試產。由於聯發科晶片組的穩健性設計,因此山寨機只需使用簡單的檢測程式,或根本不做出廠檢測而直接在交易過程中測試,省下檢測時間和成本。
因此,山寨機可以更專注在外觀設計或功能客製化。例如,推出2008年北京奧運的鳥巢、水立方、福娃等造型手機。又如,響聲特別大、讓農民放在田埂上也聽得到的手機。
當時山寨機憑藉百家爭鳴的創意、快速出貨的敏捷性及價格低廉的競爭優勢,瞄準中國二、三線城市及農村地區,以及新興國家市場。當時這些新興市場手機品牌意識不高,對手機的需求比較像大宗商品,所以,聯發科的「快老二」策略,可以滿足當時的市場需求。由於價美物廉且品質又穩定,因此在中國和新興國家市場得到廣泛的採用,也讓聯發科手機晶片銷售量跟著手機產業生態系統一起迅速成長,並成長為中國手機晶片品牌一線大廠。
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汀生(Clayton M. Christensen)曾提出「破壞式創新」(disruptive innovation)理論,說明許多市場領導者在成功之後,往往投注資源繼續精進技術、研發更完美的產品,走向「延續性創新」(sustaining innovation),不自覺地忽略了客戶的聲音,而逐漸超過客戶的需求;然而,客戶需要的往往是剛剛好、且足以負擔的產品和服務。
因此,「聯發科」以後進者,透過「低階破壞性創新」(low-end disruption)或「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」(new-market disruption),找出領導廠商(高通)過度滿足的客群或是沒看見的市場,就能以更便宜、更好的成本效益、且剛好符合這群客戶需求的技術打入市場,而顛覆既有產業的領導者。2.5G和2.75G的白牌手機和山寨機就是掌握了新興市場的缺口,並為聯發科提供關鍵的驅動技術和整體解決方案而迅速崛起。
聯發科在手機晶片產品上不是先行者、而是後進者,但聯發科以「持續性創新」來建立核心技術能力,以「破壞性創新」作為公司產品發展策略。
身為後進者的聯發科在切入市場後,能夠進而成為市場領導者,透過重組價值鏈的掌控與擴展,改寫 IC設計公司與系統廠之間原有的遊戲規則,提升系統廠自身的競爭力,為客戶縮短產品上市時間。
而聯發科的創新成功,歸功於聯發科本身札實的研發能力,要先建立研發人員在產品不同的階段,做不同任務的認知與能力,亦積極透過策略併購方式、技術授權方式、及技術合作方式來建立更完整的核心能力;另外,透析產業的發展商機,調整公司產品發展策略,創新價值鏈的多贏。
■「華為」是聯發科的貴人?!
聯發科曾帶領台灣手機零組件廠商進入大陸山寨機產業鏈中,並在兩岸產業分工之下,不僅在中國市場熱賣,更攜手相關廠商進軍全球新興市場,包括東南亞、巴基斯坦、印度……。
聯發科以中國手機「山寨霸主」起家,但智慧型手機在2011年成市場主流,山寨機、功能機逐漸沒落,聯發科開始提供平台解決方案,轉型移動處理器,但這方面著墨已久的品牌有高通驍龍、三星Exynos、華為麒麟晶片,意味聯發科在高端晶片市場充滿對手。
所以,聯發科跨入手機晶片後,相關部門連年虧損,虧3年、4年、5年,但蔡明介持續堅持,直到第6年終於賺錢。
近年,在中美貿易的緊張氛圍下,5G正處風暴核心,華為困境顯而易見。
華為一年超過台幣 3,000億的營收落入競爭者手上,聯發科亦受惠「華為」轉單效應,以「天璣系列晶片」與高通、三星在晶片市場「三足鼎立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,就算蔡明介經過10餘年的發展撕下「山寨」標籤,成功轉型自主設計,並讓聯發科成蟬聯全球前10大IC設計公司,但仍有一致命傷,即聯發科絕大部分營收在中國,不像台積電訂單來自全世界。
■華為手機全面回歸,將帶來何種震懾?
2023年9 /25日,是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回到中國兩周年,華為在這一天舉辦秋季新品發表會。在這場發表會上,Mate 60系列手機、平板電腦、手錶、智慧螢幕、耳機、智慧眼鏡等新品華麗上市。Mate 60系列告訴外界,華為已經做好回歸的準備。在此之前,華為已經蟄伏四年。
2019年 5月,華為首次被美國商務部列入「實體清單」制裁。此後所有受《美國出口管理條例》管轄的物品,美企向華為出口、再出口或境內轉讓,都必須獲得許可。負面影響接踵而來。Google宣布停止與華為合作,華為手機也無法再使用與安卓系統深度集成的 Google行動服務(GMS),直接砍斷華為在海外市場的可能性。
美方第二輪制裁也很快降臨,台積電無法再為華為代工晶片。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,華為只能盡力節省台積電在限期前趕工的晶片庫存。
海外市場受限後,華為把重心轉回中國國內。第三方市場調研機構 Canalys 的數據顯示,華為(含榮耀)2020年第 2季智慧手機出貨量在中國市場佔據半壁江山,並首度登頂全球智慧手機出貨量第一。不過,在供應鏈難以支撐的情況下,華為的市占率率很快從頂峰跌落。
華為在供應鏈受限的情況下,用了兩種妥協手段解決晶片問題:
一是不斷改善軟硬體,延長手機使用壽命,比如延伸晶片的可用性,用面積、堆疊方式換性能,用不那麼先進的工藝確保未來產品的競爭力。
另一種妥協的方式,是在高通 4G晶片解禁後,華為重啟 4G手機生產。華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推出 Mate 50 系列、P50、P60 系列。在艱難時刻,Mate50 的確幫助華為守住部分市場,但在高通供應仍有限的情況下,渠道端缺貨情況始終未緩解。長期與華為合作的渠道商說,艱難時期的華為,只能選擇保住各地區的堡壘客戶(出貨量大、華為產品比率高的經銷商),每個城市商圈基本只留一家門市。在縣城、鄉鎮等地區,大約三、四成門市分不到貨,被迫關門或轉型。
華為從來沒對「從實體清單中出來」抱有任何幻想。如何在制裁常態化下維持正常運營,才是核心問題。
2023年4月,華為宣布實現自主可控的 MetaERP 研發,並完成舊 ERP系統替換。這是最關鍵的企業級 IT應用,也是華為企業經營最核心的系統。此前中國還沒研發出能夠滿足如此大規模跨國企業使用的 ERP系統。
接著,華為採取低調姿態手機業務回歸。Mate 60在沒有任何提前預告的情況下發售,甚至沒有寫明晶片配置,但 Mate 60 卻獲得史上最高的關注度。大量拆機與測速影片似乎已經說明,Mate 60 實際體驗已經超出消費者預期。
尤其,Mate 60系列,國產化率已經超過 90%。至少有 46 家供應商、一萬多種零件來自中國,也是目前國產化比重最高的手機。
華為手機從2023年秋天開始啟動全面回歸戰略。中國國內渠道與供應鏈已經為此做好準備,此後,海外回歸也只是時間問題。
雖然,擺在華為與整個國產供應鏈面前的挑戰仍然艱巨,但可以確認的是,華為在封鎖中快速自我造血、活了下來,並且又站回熟悉的起跑線前。
四、大陸國產積木市場吟一段「進口替代」的低調
很長一段時間裡,中國積木背負著「山寨」、「劣質」、「低價」的罵名。
例如說到積木,多數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想到玩具巨頭「樂高」,且它一直是高價玩具的代名詞。
但現在,樂高和中國消費者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,因為它的價格越來越貴,讓人望而卻步。2022年 8月,樂高宣布全面漲價後,中國消費者不得不將目光轉移到更具性價比的「平替」上,這恰好給了中國國產積木一線機遇。
如今,中國國產積木正展現著蓬勃的生命力,透過 IP合作,及精益求精的技術研發,並朝創意潮玩、收藏積木等方向轉型。
再提個「冷知識」,中國不僅擁有全球最強的玩具供應鏈,且全球超過 70% 的玩具都產自中國。只是,原本皆走「代工」的經營方向。
目前,中國已經成為積木玩具最大消費國,預估2023年中國積木玩具產量和國內需求量將分別達到 6.57億套和 3.25億套。隨著「內需」崛起,中國積木得以更快速地滋養、建立本土品牌,例如星堡、Keeply。
尤其,國產積木在打造本土 IP上有共同的文化記憶,也更加深入人心,例如故宮、四合院、十二生肖等已經成為各家積木玩企的標配主題,這原本就是國產積木品牌的一大本土優勢。
當然,目前國產積木市場雖百花齊放,但「同質化」的問題卻必須留意。
例如2021年初,國產積木花走俏路線,行業迅速掀起一波「花」主題市場熱潮,多數本土企業推出的玫瑰、向日葵、康乃馨等常見花卉,但最終拼出來的成品,不論外觀還是顏色,都大同小異,「撞設計」的情況屢見不鮮。
除此之外,國產積木的品質、品控與細節,與樂高仍然有不小差距。
其實,決定積木品質的無非四個因素:原料、注塑機、模具及流程監控。
樂高工廠所用的注塑機,和大多數國產積木並無二致。在原材料上,新興國產積木品牌也都符合玩具級安全標準。真正影響國產積木品質的原因,還是模具。例如樂高的零件模具成本高達 25萬歐元,相關模具已經積攢超過 7,000 套,這種經年累月所構築出的「護城河」,國產積木一時很難趕超。
因此,國產積木產業不想坐以待斃,就必須在文化創意、數位化、智慧化、高精度等方面下功夫,將視野看的更深遠、更具體。尤其快速建立配套企業,如積木標準化精密通用件的專業供應商 「高德斯」,就已與多家國產積木品牌建立長期戰略合作關係。
例如原料供應上,高德斯引入世界一流的自動供料生產設備,可以實現五十多種配色原材料的自動化烘乾和智慧分配;並在生產後的收納階段,全程隔絕人手參與,避免打包過程接觸外界汙染;而後自動裝箱貼碼掃碼,送到電商智慧倉。目前高德斯每年可生產積木零件超過 100億顆,未來幾年內產能甚至有望趕上樂高,且所有積木製造公差均在 ±0.01mm 以內。可以說,在品質上,國產積木已經邁出一大步。
不過,國產積木僅僅做到這些,還不足以與樂高抗衡。樂高幾十年如一日的深耕,以及持續輸出的「積木文化」,讓樂高早就超越了「玩具」的定義,成為了當代流行文化符號,更有著一般玩具無法比擬的高接受度。這並不只是關乎資金和決心的問題,而是來自於時間的沉澱。龐大用戶基數和品牌影響力,都非一日之功,國產積木還需戒驕、戒躁。
無論如何,國產積木與樂高之間,未來也終有一戰。
五、跋尾—以「破壞式創新」理念,走向藍海市場
1997年創新大師克雷頓.克里斯汀生(Clayton Christensen)在《創新的兩難》的著作中提出「破壞式創新」(disruptive innovation)概念。
蘋果(Apple)創辦人史蒂夫.賈伯斯(Steve Jobs)曾說,書架上唯一的一本商業管理書就是《創新的兩難》;英特爾(Intel)創辦人安迪.葛洛夫(Andy Grove)、亞馬遜(Amazon)創辦人傑夫.貝佐斯(Jeff Bezos)、網飛(Netflix)創辦人里德.海斯汀(Reed Hastings)都是他的信徒,貝佐斯和海斯汀更要求高階主管閱讀他的著作。
克里斯汀生一生鑽研「創新」,他的名著《創新的兩難》研究各個產業的龍頭企業,像是硬碟業、電信業、汽車業等領域龍頭企業,為什麼時刻保持警覺、立即回應顧客,卻還是在面對科技和市場變遷時,喪失領導地位?
為什麼這些原先績優企業信奉的原則,包含創造最大利潤的產品、改善主要客戶的需求,反而成為削弱競爭力的主因?
克里斯汀生這個「破壞式創新」概念一提出,旋即獲得企業廣大迴響,27年過去,到現在仍然適用。
■何謂「破壞式創新」概念?
一般來說,企業總是專注現階段消費者的需求,不斷增加、優化功能,推出規格更好的延續性創新(sustaining innovation),像是 iPhone 自第一代推出以來,到現在已推出至 iPhone 15。
反向思考—「破壞式創新」指的是,後進者推出產品或服務性能剛好、價格便宜,吸引那些市場龍頭沒看在眼裡的客群,逐步蠶食進攻,等到龍頭企業意識到威脅,卻為時已晚,而後進者最後也因此趕超產業龍頭。例如,拼多多對抗阿里巴巴的戰役。
又如,台積電的崛起,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
在台積電創立之前,傳統的半導體廠一手包辦晶片設計、製造、封裝、測試、銷售。
1987年,張忠謀創立台積電時,一開始是提供性能夠好、價格便宜的晶圓製造服務,當半導體業走向垂直分工,無晶圓廠晶片設計公司專注設計晶片,再委託台積電生產製造,無需承擔製程技術、工廠營運等成本。
之後,台積電持續改善其晶片製造能力,逐步轉變為提供性能優良、價格昂貴的晶片製造服務,近年更迎頭趕上英特爾,成為產業領導廠商。
台積電逐步蠶食進攻,改變了半導體產業的商業模式,更開闢了更好的供應鏈管理服務的市場。
但是,不是所有產業競爭的突破,都能被歸為「破壞式創新」。
舉例來說,很多人認為 Uber用 App連結有乘車需求的消費者,以及願意提供服務的駕駛,已構成破壞式創新,但克里斯汀生卻否定這樣的說法。
「破壞式創新」的發展機會,來自於低階市場或新市場;一開始訴諸低階或未被滿足的消費者,才移往主流市場。例如,聯發科對抗高通的戰役。
而Uber 的方向恰好相反,提供的計程車服務本來就是主流市場需求,鎖定對象也不是非消費者,Uber 的顧客本來就有叫車習慣,它是從主流市場逐漸擴張至被忽略的區塊。
■在「現有市場」中「尚未被滿足」的顧客,努力提供「尚未被滿足」的顧客更好的產品與服務
如果競爭對手誤解 Uber的革新模式,擬定策略的效益可能大打折扣。
這也是為什麼克里斯汀生多次提醒,先了解創新的精髓,才能正確應用它的原則。因此,克里斯汀生的第一門課,教的不是如何「做到」創新,而是如何「定義」創新。
克里斯汀生認為,創新不必然需要高科技,也不等同創造新事物,「創新」是組織如何將勞力、資本、資源和訊息,轉化為「高價值」產品或服務的過程。
克里斯汀生持續尋找創新的突破口。他提及,創新不只理解顧客需求,重要的是顧客「選擇產品的原因」,也就是顧客使用「產品的用途」,以此為基礎,更能研發更適切的產品。
「破壞式創新」的主要策略,是將產品或是服務,以價格低廉、性能較差(但足夠使用)的產品,爭取在位廠商的低階顧客,待技術進步、逐漸提高產品性能後,便能以低價優勢席捲高階市場,一舉取代舊產品。亦即,「破壞式創新」是把焦點放在「現有市場」中「尚未被滿足」的顧客,努力提供「尚未被滿足」的顧客更好的產品與服務,進而突破現有市場所能預期的消費改變,擴大和開發新市場。善用「破壞式創新」的策略,可開發深層商機
《哈佛商業評論》前總編輯凱倫.狄倫(Karen Dillon)表示,克里斯汀生留給世人最重要的一件寶物,其實是「如何真正的思考」,且是教我們「如何思考問題。」

 微信
微信